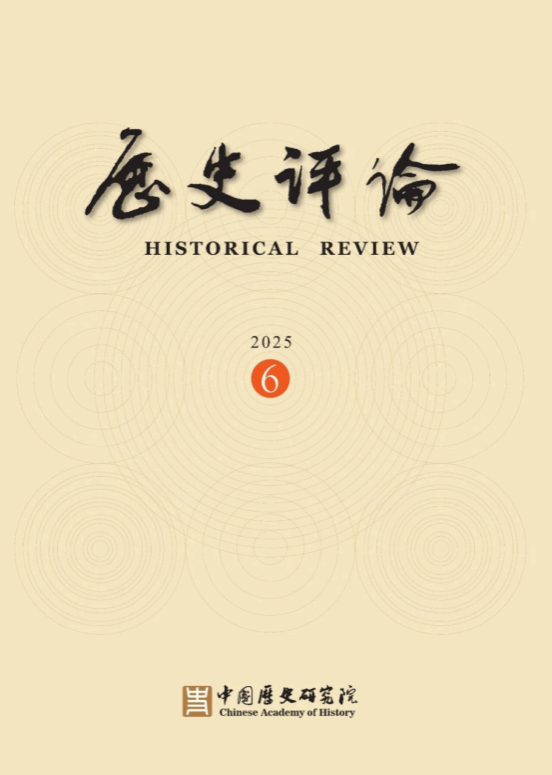
历史上新疆与中原的宗教联系从未中断。伊斯兰教的传入没有改变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更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特质与走向。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方向,也决定中国各宗教多元并存的格局。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交融共存成为历史上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阐明新疆各宗教的发展历程,对于驳斥“三股势力”、“双泛思想”所谓的“一教独大”谬论具有重要意义。
原始宗教历史悠久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新疆先民相信万物有灵,最初的宗教观念由此产生。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增强,新疆地区的部族各自形成多样的信仰对象。这些信仰以自然崇拜为主,包括动植物崇拜、日月星辰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
黠戛斯人(柯尔克孜族的先民)普遍崇拜动物,尤为崇拜狼,并以狼为图腾。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有多处将英雄玛纳斯比作“青鬃狼”的描述,如“青鬃狼英雄玛纳斯,随身带领四百八十名勇士”,“青鬃狼玛纳斯策马出击,太阳般的脸庞闪烁光芒”。在现今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以狼骨作为辟邪的护身符。
古代于阗盛行老鼠崇拜,《北史》记载,于阗“其王姓王,字早示门。练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练锦帽,金鼠冠”,显然是远古鼠崇拜的遗存,这一习俗即使在于阗人普遍信仰佛教之后仍然存在。20世纪初,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一块鼠头神像的木板画,是古代于阗人老鼠崇拜的直接证据。
随着生产力进步,新疆先民的原始崇拜逐渐演变为萨满教。萨满即汉语中的“巫”。“巫”字本义为沟通天地之人,故而萨满在部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详细记载权力移交的萨满仪式,“在大帐右方立了四十庹长的一根木杆,杆顶上挂着一只金鸡,杆下拴着一只白羊。在左方也立了四十庹长的一根木杆,杆顶上挂着一只银鸡,杆下拴着一只黑羊”。立木杆于大帐两侧,并挂金鸡、银鸡于杆顶,拴白羊、黑羊于杆下的远古仪式规范,如今发展为悬挂羊头、牛尾、布条等器物。南疆的麻扎(纪念冢)仍存有插各色旗幡、挂牛马尾、供野羊角的习俗。萨满在哈萨克传统社会中曾经扮演过部落头人(el basi)、军师(ahelchi)、民间医师(emshi)等角色。哈萨克族有句俗语:不信卜言,但不能无卜(balgha senbe,balsiz jurme)。在改信伊斯兰教后,萨满借助伊斯兰教隐藏自己的身份,以民间医师、占卜师等多种身份在社会中活动。每逢古尔邦节,新疆各族群众会跳起“萨玛舞”,“萨玛舞”就是由“萨满舞”演变而来的,足见萨满文化在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中的遗存。
多种宗教共存
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历史上新疆宗教格局的特点,交融共存是历史上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是祆教。祆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公元前4世纪随游牧部族的迁徙传入新疆,主张善恶二元论,崇拜圣火。祆教在新疆与其他宗教并存,可以通过文献窥见。《北史》记载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中“天神”指的就是祆教天神,“兼”字尽显祆教与佛教并行不悖的宗教和谐共处景象。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卷二的题记中有“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的记载,“胡天”指祆教天神或祭祀祆教天神的场所,而《金光明经》是典型的佛教经文。《宋史》记载高昌“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在高昌回鹘时期,祆教虽然衰败,但并未绝迹,与摩尼教、佛教并存。
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4世纪至10世纪,佛教在新疆进入鼎盛时期。由于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原的主要通道,西域佛教与中原佛教的交流十分频繁,中原名僧多经新疆前往古印度求取佛法,西域各僧自新疆到中原弘扬佛法。前者的代表是法显、玄奘等,他们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如《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后者的代表是鸠摩罗什、佛图澄等,他们译介佛教经典,翻译大量佛教典籍,如《金刚经》《维摩诘经》等。
唐朝对道教的尊奉,促进道教在新疆的发展。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年)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文子》为《通玄真经》。此书以老子之言为教,杂糅名、法、儒、墨诸家。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就出土《通玄真经》的《九守》篇残片。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道教符箓及大量随葬衣物疏,其中永徽六年(655年)《赵羊德随葬衣物疏》中有“急急如律令”,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并于10世纪中叶对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历时40余年的战争,最终在公元11世纪初攻灭于阗,结束和田地区千年以来佛教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既有抵制,也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喀喇汗王朝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著作《突厥语大辞典》中收录“萨满”、“僧人”、“上苍”等词条,是驳斥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伊斯兰教谬论的证据。这也侧面印证,即使喀喇汗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也不得不正视新疆自古以来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至16世纪初,伊斯兰教传播到整个塔里木盆地和北疆、东疆部分地区,新疆形成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
17世纪后,卫拉特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在新疆地区流传。清乾隆时期统一新疆后,道教与关帝信仰一度复兴。由于关帝信仰具有深厚的“忠君”内涵,因而得到清廷重视。新疆屯垦戍边军队所在之地必有关帝信仰,为维系新疆移民社会稳定发展、构建大一统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回疆通志》记载,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乌什、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均建有万寿宫、关帝庙。洪亮吉《天山客话》描述清朝统辖下的新疆,“塞外虽三两家,村必有一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盖接于西海云”。
伊斯兰教深受其他宗教影响
尽管今天的新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但历史上新疆的主要宗教发生过多次变化,新疆的伊斯兰教也受到其他宗教影响。
伊斯兰教苏非主义(al-Sūfiyah)在新疆传播过程中,充分吸收万物有灵论、祖先崇拜、动植物崇拜,甚至祆教的圣火崇拜。“苏非”一词一般认为源自“苏夫”(Sūf),该词是阿拉伯语“羊毛”的音译词。苏非主义的修持者强调简朴、清贫、苦行、禁欲的宗教生活,在衣着上厌弃对华丽服饰的追求,沿袭穿羊毛衣的传统。新疆的苏非教团乌瓦伊西耶(Uwayshlyyah)主张朝拜麻扎,并将其视为接近神的功修方式。乌瓦伊西耶把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布格拉汗尊为圣人与本派的保护神,萨图克·布格拉汗的麻扎也成为该派信徒朝拜和修道的主要圣地。上述例证体现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对新疆先民祖先崇拜的吸收借鉴。
尽管佛教作为新疆主要宗教的地位被伊斯兰教取代,但是新疆的清真寺古建筑内却发现具有佛教意蕴的符号,如佛教的吉祥标志“image.png”字符、盘长纹、莲花纹等。“image.png”字符本源于史前时期,左旋和右旋皆可,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古代婆罗门教、耆那教都使用过这一标志,后被佛教借用,寓意为万德齐聚,古代译为“吉祥海云相”。又如盘长纹,也称吉祥结,为佛教法器八吉祥(八宝)之一,其绳结形状连绵不断、无始无终,象征佛法回环贯彻、长久永恒。盘长纹在民间演化为中国结,承载家族兴旺、富贵绵延的吉祥寓意。佛教还视莲花为圣物,佛教经典《法华经》全称为《妙法莲华经》,以莲花喻妙法,经云“为诸声闻说是大乘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故而佛寺中也常以莲花纹用作装饰纹样。上述极具佛教意蕴的符号,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加满清真寺中均有呈现,反映不同宗教在共存中的相互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中期,魏晋时期传入新疆,在5世纪已广为流行。楼兰遗址出土的彩绘木棺两端描绘朱雀与玄武;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书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张定度李坚固”等文字,另有道教符箓、黄纸、朱书出土,其上画有持神物的神像、写有“天帝神”等字样。阴阳太极图是道教的核心象征之一,直观体现道教的基本思想和教义。明末赵仲全作《道学正宗》载有“古太极图”,并划分八区,与现今流传的圆圈内有一对首尾互抱的阴阳鱼,双鱼又走成一个S形曲线的太极图大有不同。而南疆喀什地区泽普县始建于清代的麦德里斯遗址的门楼穹顶,正绘有道教“古太极图”,可见道教的影响。
综上所述,历史上新疆与中原的宗教联系从未中断。伊斯兰教的传入没有改变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更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特质与走向。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